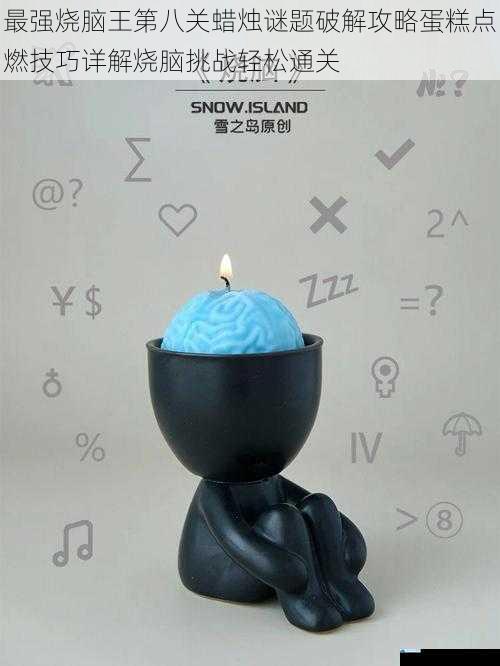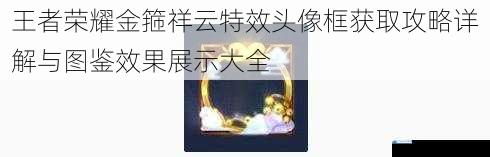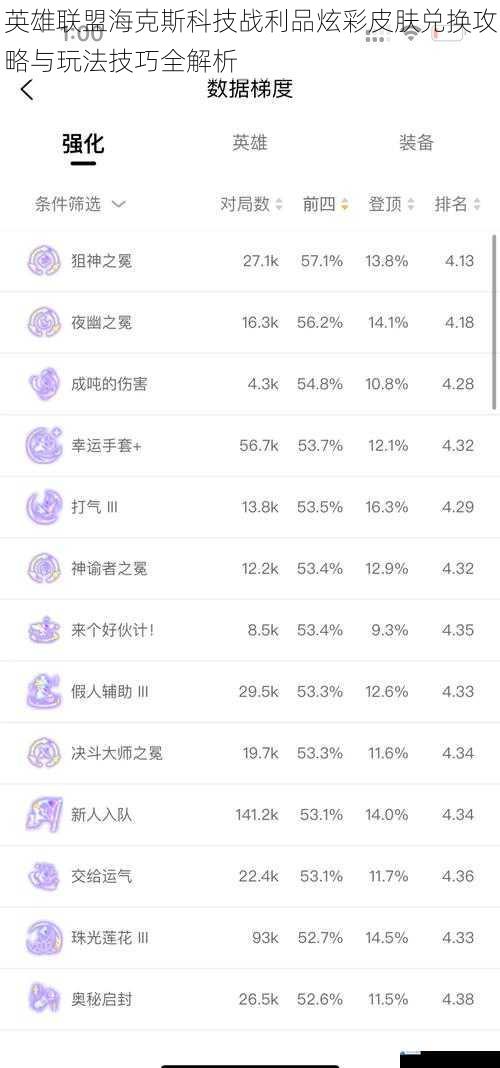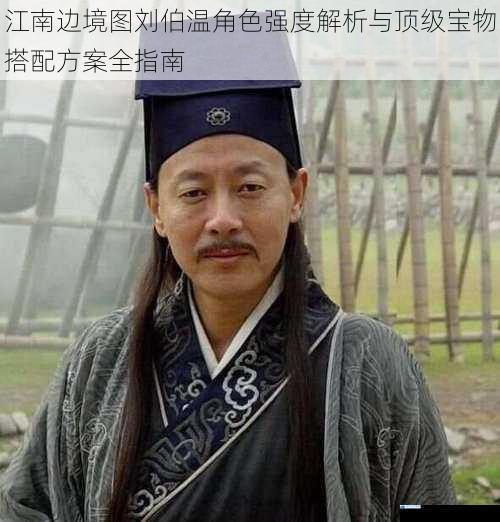扇子作为人类最早发明的纳凉工具之一,其制作材料的选择深刻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物质条件与技术发展水平。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竹编器物残片,为探索扇子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将从考古发现、文献记载与工艺传承三个维度,系统考证中国古代早期扇子的制作材料及其文化内涵。
新石器时代的竹制器物遗存
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竹编席纹陶器上,清晰可见以竹篾编织的几何纹样,印证了距今5300年前长江流域已形成成熟的竹材加工技术。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发现的苇编残片,虽已炭化但仍保持着清晰的经纬结构,证明中国先民在7000年前已掌握植物纤维的编织技艺。这些考古发现为竹制扇骨的早期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。
竹材因其纤维纵向排列的特性,在劈裂加工中可形成均匀细薄的篾片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战国竹扇(图1),扇面呈梯形,以细密竹篾编织出菱形花纹,边缘用漆木条加固,整体厚度仅0.3厘米。这种"便面"形制的竹扇,印证了国语·楚语中"扇暍"记载的真实性,其制作工艺之精良远超单纯的生活用具范畴。
甲骨文中的造物密码与礼器演变
商代甲骨文"扇"字()象形手持长柄羽具之状,与小尔雅·广服"大扇谓之翣"的记载相符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内戈,其木柲表面残留的羽饰痕迹,证实了商代贵族仪仗用具中羽毛装饰的普遍性。这种礼器化的装饰传统,为后世羽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周礼·天官记载的"掌扇"官职,其职责包含管理王室仪仗用具。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宴乐纹饰中,常见侍者执长柄羽扇随行的场景。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铜器架座人物,手持的羽扇长度达1.2米,羽毛呈放射状排列,这种规制化的礼器造型,标志着羽扇已从实用工具升华为权力符号。
植物材料使用的民俗记忆
诗经·邶风"淇奥"篇中"绿竹猗猗"的记载,反映了早期竹材使用的普遍性。而树叶作为临时性纳凉工具的证据,更多见于民俗学调查而非考古发现。云南沧源崖画中的持叶人物形象,可能与热带地区的特殊生态环境相关,但缺乏实物佐证。
从材料特性分析,竹材的纤维结构使其具备良好的抗弯强度,单根竹条可承受300-500MPa的弯曲应力,这是制作扇骨的关键物理属性。相比之下,树叶的纤维素含量虽高(约40-60%),但其各向同性结构难以形成稳定支撑,更多作为临时性的纳凉工具使用。
工艺传承中的技术选择
汉代说文解字将"扇"释为"扉也",暗示其开合机制与门扉的相似性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汉代"便面",采用漆木框架固定素绢扇面,这种复合材料的运用标志着制扇工艺的重大进步。而同期出土的竹扇实物,其篾片宽度已精确控制在0.15-0.2厘米之间,与现代手工竹编的工艺标准相当。
唐代唐六典记载的进贡清单中,既有"竹丝扇"亦有"孔雀翎扇",说明不同材质的扇具已形成明确的功能区分。宋代东京梦华录描述的市井"细竹扇",与苏轼"轻扇破微凉"的诗句相印证,展现了竹扇在民间的普及程度。这种工艺分野,本质上反映了材料特性与文化功能的深度契合。
综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,中国古代扇子的材料选择经历了从竹材基础应用,到羽毛礼器化发展的演变过程。竹材以其优良的物理特性和加工便利性,成为最早被规模化使用的制扇材料,而羽毛因其稀缺性与装饰性,主要服务于礼仪需求。这两种材料的并行发展,共同构建了中国扇文化的物质基础,也为后世书画扇、工艺扇的出现提供了技术准备。树叶作为临时性代用品,更多存在于特定生态环境下的民间记忆之中。这种材料选择差异,深刻映射了中国古代社会阶层分化与技术进步的双重轨迹。